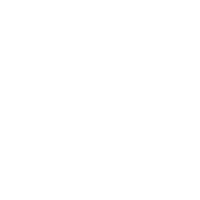“小时候玩过斗蛐蛐吗?”倾月似无限享受这大自然最天籁的鸣唱,笑着问信阳。
“很少玩,小时候功课太多,母后又管得紧。”信阳道。
“呵呵,那现在可没人敢管你了,我们来玩一回,回味一下童年时的那份快乐,怎么样?”倾月亮亮的眸子里憧憬流光。
“好啊,你要玩我便陪你玩!”信阳自然不会扫倾月的兴,宠溺地答应。
“慢,玩就来真格的,斗赢斗输可得有个说法!”倾月一本正经道。
“什么说法?”
“输的人必须满足赢的人一个愿望!”
“呵,这赌注好!”信阳立即来兴趣了,眉目闪耀着兴奋的光彩,“但是我得问一下,只要是愿望都给满足?”说到此间,信阳贼兮兮的眼瞟向倾月衣领里半掩半露的漂亮锁骨,暗咽了下口水道。自倾月病见大好,他的那颗**之心早就蠢蠢欲动了。
“无论什么,都满足!”绝色的眸光里邪魅一闪,暧昧便如夜色里的荷香,袅袅流散,“不过,我们可要讲好,蛐蛐得自己抓,不许人帮忙,还有愿赌服输!”
“嗯嗯,自然是愿赌服输!”信阳浑身血脉偾张,心更如猫抓。
于是整个山庄的侍婢兵丁看到了这样啼笑皆非的一幕,他们高高在上令人望而生畏的王爷,提着灯笼,撅着屁股,跪趴在地上,草丛里,墙角处,井栏边,一个一个锲而不舍地翻了遍,最后弄得浑身脏乱,一张脸汗灰斑驳,活像一只花猫。
“抓到了吗?”早在屋中等候的倾月见一身狼狈,但脸却大放喜光的信阳冲进屋里,笑嘻嘻问道。
“抓着了,很大个的!”信阳捂着临时抓蛐蛐的工具——笔筒兴奋地道。
“倒出来看看!”
“好咧!”
倒在陶器里,借着灯光一看,见那蛐蛐头圆,胸宽,果然是个大个。
“哈哈……”谁知倾月一见这蛐蛐,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信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笑什么?“
“哈哈……你自己看了就知道了!”倾月说着将自己抓的蛐蛐倒入陶器中,两蛐蛐一见面,互相嗅了嗅,居然卿卿我我起来。
“我操,居然是只雌的!”信阳立即黑了脸,大暴粗口,一把捞起那雌蛐蛐,狠狠摔在地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居然抓了个母的,愤怒与尴尬可想而知。
“哈哈……”倾月在一旁笑弯了腰,下人们则想笑不敢笑,憋得甭提多难受。
“王爷,密报!”一个侍卫忽在此时匆匆而来,递上一份密函。
挥退下人,信阳拆开细看。
“王爷,何事?”倾月看他的脸色有些沉重,不禁问道。
“义顺帝重病。”
“小皇帝身子一样健康得很,如何突然病重了?消息可靠吗?”倾月疑惑道。
“绝对可靠,是我太医院的心腹写的密函。他说晚间义顺帝吃了半个西瓜就突然口吐白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有人下毒吗?”倾月一惊。
“极有可能!”
正说着,侍从又来报,宫内太后身边的总管太监快马加鞭而来,似有急事。
信阳见召,结果一问之下,果然说的是义顺帝病重的事。
打发了太监,信阳立即命人备马去往宫内探病。毕竟他是臣,人是君,何况这重病病得蹊跷,极有可能他人谋害,他必须连夜进宫查探个清楚。
“王爷,我同你一起去!”倾月请求。
“倾月乖,好好呆在这里等我回来。此去王城少说也有二十里路,你身体还没完全复原,禁不起如此颠簸!”信阳自然不同意,柔声劝解。
“你又扔下我一个人!”倾月生气了,手在桌子上用力一挥,装蛐蛐的陶器立即坠地,四分五裂。
“好吧,好吧,我带你去!”信阳无奈,只得退步。
马车行驶了大半个时辰进得宫廷。
一路上,太监宫女挑着宫灯,护着信阳与倾月急匆匆前往小皇帝寝宫。
才到得宫门前,已听得太后呼天抢地的哭闹声。
进得宫,发现寝宫内乱成一团,太医们聚在一起面色凝重商议,宫女太监们则齐刷刷地跪在面色个个惨白,不知自己命运,而太后则抱着小皇帝,拍打着床在那大声哀嚎。
“别哭了!”信阳厉声一喝,寝宫内陡然死一般寂静。
电光火石间,太后与倾月对了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于是太后装模做样掏出手绢擦泪。
蓦然间,宫门倏然砰然关上,这轰鸣的一声倏然成了动手的暗号,但见所有宫女太监太医面色齐齐突变,刷刷刷,寒光闪烁,利器森然于胸前,呼喝着便往信阳与倾月攻来,而太后则抱起小皇帝立即从偏门退出。
好个胆大妄为,虎毒食子的女人!信阳怒意磅礴,他远远低估了她的实力与胆魄,竟然用这样的阴毒之计诱他入宫,冒此成功便成王,不成功便是死的天下第一大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