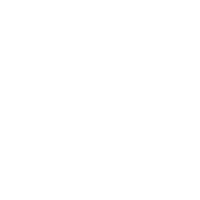刘牧之抱着妻子的尸体。
脸上不见哀戚,只被莫名的茫然所充斥。
直到孙儿开始哭泣。
悲伤才迟迟传递过来,他一下湿润了眼眶,轻轻呼唤着妻子的闺名。
熟悉的温柔回应忽自怀中响起。
“郎君。”
他惊喜低头。
“娘子,你没……”
一对嵌在死灰面孔上的充血眼球直勾勾对着他,血液渗出眼角流淌染得嘴唇鲜红。
温柔声音骤然尖利。
“为何要害死我?!”
毛发顿时倒竖。
刘牧之猛地推开尸体,护住孙儿,一把抓起腰间金瓜。
正高举,再看去。
妻子双目紧闭,面容端庄如故,哪儿有血泪流淌?
幻觉?
“父亲?父亲!”
屋外传来呼喊,却是一向循规蹈矩的儿子披头散发怀抱着个圆滚滚的事物跌跌撞撞冲进来。
刘牧之习惯性地要呵斥,可一扭头——儿子衣衫满是血污,而那圆形事物分明是一颗人头,仔细看,是自己的儿媳。
“你……你做了什么?”
儿子举起人头,仿佛在夸耀什么功绩。
“父亲又糊涂啦?咱们要予法王请罪,自得备上大礼。”
说着,瞧见母亲的尸体,更是大喜过望。
“母亲死啦?倒也省事。”
便把人头系在腰间,掏出把短刀,兴冲冲过来。
“逆子!”刘牧之惊骇莫名,“住手!”
儿子果然罢手,却道:“是啦,为人子女怎可毁坏父母遗容?”
目光一转,落在孩子身上。
“哎?这小畜生细皮嫩肉拿去送礼岂非更佳?”
说罢一把揪住孩子总角,眉开眼笑着竟是要当场割取轻声孩子的头颅。
刘牧之大惊,情急之下,拿金瓜砸倒儿子,抢过孙儿撞门而出。
留得身后。
“父亲。”
儿子抱着人头瘫坐在地叫唤着。
“你要害死我们吗?”
刘牧之浑身冰寒,奔逃愈发狼狈。
慌张跑出后院。
“来人,来人……”
呼呵几声,愕然见着廊中积血成泊,随他转战多年的亲兵竟在互相砍杀,兵刃卡在骨头拔不出,便野狗般用牙齿来撕咬。
惶惶路过庖厨。
烟气自半开房门里滚滚而出。
大锅腾腾冒着白气,烟笼雾罩里,伙夫、婢女们把自个儿用铁钩吊在房梁上,同腊肉熏鸡挂在一处,一扇一扇齐整排列。
惊骇逃至中庭。
供奉多年的老法师宛若疯魔,四处抓人,凡被他攥住,便用铁锥刺烂双眼,挑破耳膜。
刘牧之不敢停留,抱紧孙儿,小心绕开。
可他很快发现,府中各处不是在自相残杀便是以各种方式自戮,惨叫避无可避,哀嚎躲无可躲。
疯了?都疯了么?看,天亮了,天已经亮了,已经是白天了!
刘牧之语无伦次地嘶喊着,可无人理会他,他的子女、他的妻妾、他的部下、他的奴婢……身边的一切人等,除了他与怀中的孙儿,统统陷入了凄惨的癫狂中无法自拔。
直至。
“东主。”
他猛回头,老供奉紧闭着双眼出现在面前。
不等他下意思挥出金瓜,耳边:“听我说!”
“护宅法坛已为恶鬼所破,老朽撑不了多久。”
“可规矩……”
“狗屁规矩!”
老供奉喉头像含着血,字字含混又滑快。
“眼下动手的应是‘替生’、‘换死’两头大鬼,‘替生’有目即可乱人心智,‘换死’有耳即可惑人魂魄。欲保存性命,当……”
最后一句,老法师几度张口,也是无声。
刘牧之急切追问:“当如何?”
老法师忽的上前,将滴血的铁锥塞给刘牧之,翻开眼皮,但见其两个眼洞中皆是血肉模糊。
眼球已被捣成烂肉。
刘牧之饶是沙场宿将,冷不丁也被眼前吓得连退两步。
老供奉没紧随上前,他用手指抵进耳朵,用力一捅。
同时张口呼喊,虽不闻声,却分明是:
“逃!”
刘牧之楞了稍许,转身埋头狂奔。
他逃至前院,百十步外见着一面影壁,影壁便是大门。
可这时,被他抛到身后的哀嚎与惨叫却追了上来,如有实质,扯住他的衣袖,绊住他的脚步,于是这短短百十步好似被无限拉长,怎么也跑不完。
那些哀嚎,那些悲鸣,也伴着钟声越来越清晰,汇成句句质问。
“刘牧之!你要抛下我们吗?”
“刘牧之,为何要害死我们?!”
“刘牧之,你可知罪!”
字字句句叫他脚步愈发沉重,喘息愈发急促,终于,他狠咬舌尖,铁锈味儿溢满口腔换得些许清醒。
他拼命一挣。
跑不尽的百十步竟骤然缩短,那面影壁突兀撞到眼前。
意外的。
浑石雕成的影壁此刻却如沙筑土堆,一撞便碎,露出其后早已洞开的大门。
可门外却非熟悉的街景,唯见着重重楼阙盘山而起,巍峨入云。
刘牧之此生从未见过这般宫厥,哪怕梦里,可此时,他却喃喃着一口道出了其名字:
窟窿城。
耳畔的钟声还在响起,一声漫长过一声,仿佛永无尽时。
身后的哀嚎与质问再度追了上来,纠缠不去。
“刘牧之。”
他神情一怔,木木低头。
被一直护在怀中的孩子笑着问他。
“你可知罪。”
他惊慌抓起铁锥,在孩子眼耳边游移颤抖一阵,终究哭叫一声,丢开了铁锥。
无力跪倒下去,重重磕头。
“知罪。”
“知罪!”
“刘牧之知罪!”
碎石划开额头,鲜血和泪淋漓。
“只求法王慈悲饶我孙儿一命。”
…………
当钟声响尽。
人们看到的是磕烂了脑袋、跪死在大门里的刘牧之。
消息传得很快。
门前聚起愈来愈多的人。但没有喧嚣,只是抑声低语,或干脆噤声,更没人敢踏入大门一步,本该喧闹的白日,沉寂仿佛深夜。
依着惯例。
凡有横死家中,总会有僧道前来超度亡人,会有差役入场收敛尸身。
可今日却一概皆无。
这可是郡公,是左仆射,是节度使。
纵然已兵败失势,却仍是钱唐官面上有数的高官显贵。
竟由着他曝尸于人群的围观么?
“高官如何?”
“显贵如何?”
“声名再盛,胜得过法王之威?权势再大,强得过鬼神之力?”
几个无赖汉守在刘府边上,领头一个大声嚷嚷着,在一片低语中分外刺耳。
“凡夫俗子,住了大宅,穿了紫衣,使唤得几个奴仆,自以为成了人上人,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来触犯鬼神威严,落得这般下场,岂不活该?岂不可笑?”
人群里不少各方派来的耳目,其中不乏“达官显贵”,听着这以下犯上的粗鄙话语,一阵哄闹,但终究无人敢冒头反驳。
人群不起眼的边沿。
闻讯而来的李长安作脚夫打扮,拿汗巾缠住小半张面孔。
“他既自暴身份,我以为已做足了准备?”
同样得信赶到的无尘,同样改换了面目,此时腰佩长剑,头戴斗笠,仿佛江湖豪客。他神情凝重,小声应道。
“刘施主确已有所防备,可哪知恶鬼竟坏了规矩,胆敢白日杀人!”
“规矩?十三家怎么说?”
“祖师们各有考量。”
“所以连收尸的也无一个?”李长安摇头,“前脚露了脸,后脚就灭了门。你的谋划怕要落空。”
“不然。”无尘立时言道,“做了解冤仇,岂有退路?他们都是聪明人,会想明白的。”
“想得再明白又如何?有刘牧之前车之鉴,谁再肯相托腹心?军合力不齐,如何与恶鬼相争?”
无尘张了张口,反驳在喉间几度回转,终究化作一声叹息。
“只好再作计议。”
人多眼杂不是谈事的地界,两人正要退去。
刘府前,那无赖汉还在喋喋不休。
“这刘牧之好端端的富贵老爷不做,学人做什么‘解冤仇’。不错,就是那些阴沟里的老鼠,藏头漏尾的贼匪,沆瀣一气,四处作乱,自以为得势,结果呢?”
无赖汉啐了口唾沫,招呼同伴拿来碗饮子,补充口水。
“别看他死得凄惨,却也是法王慈悲。告诫某些人,什么事做得,什么事做不得,免得一朝连累家小、亲朋,成了孤魂野鬼,夜夜哀哭,向你讨命。”
仿佛应和话语,大街上竟真的听着低低的哭泣与惨呼。
细细听,分明来自大宅深处。
人群顿时哗然。
平旦才死,尸体或许还尚温,青天白日的就要作祟了么?!
“莫慌,莫怕。”
无赖汉却得意笑道。
“法王慈悲,只叫刘家人死了一半,里头呀不是死人在哭,不过是活人在叫。”
说罢。
刘牧之身旁那具小小的“尸体”颤了颤,接着,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蹒跚两步,却又跌倒在碎石里,探出小手茫然摸索,稚嫩的声音哭喊着:
“阿翁,阿婆……”
人群里颇有不忍,可谁也没上前,反而愈发屏息禁语,好似生怕吭出点声气,便会叫那孩子误以为是回应,纠缠过来,惹得鬼神误会。
其实大可不必。
那孩子的眼耳边渗出条条血痕,显然,耳已聋,眼已瞎。
李长安顿住了脚步。
“道长,莫要冲动,这是陷阱!”无尘急道,“潮义信在周遭布下许多好手,地下还定有大鬼埋伏,就等人自投罗网。”
“我晓得。”
李长安点了点头。
“和尚你说得对,做了解冤仇,岂有退路?”
又扯下汗巾,露出面容。
“刘牧之说得也没错,欲登高一呼,又怎可藏头漏尾?”
“等等。”
无尘神色变幻一阵,重重吁出一口长气。
“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