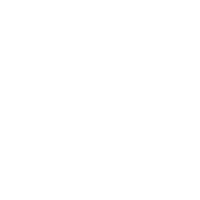“好!”耶律德淡淡地应了一声,趾高气扬地在前,耶律光随后,月羲最后,三人去往里屋。
“哥哥!”蓝霁儿嘟起嘴拉住了月羲的袖子。
“丫头乖,哥哥有要事不能陪你,你再去玩会,晚间的时候我陪你吃饭!”月羲侧身抚摸了一下蓝霁儿的脑袋,水润水润的眸子里俱是溺死人的温柔,让蓝霁儿的委屈只能又咽回了肚里去。
“丫头最乖了!”月羲宠溺一笑,然后转身离去。
“哼!”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蓝霁儿狠狠吸了吸鼻子,气鼓鼓地用力揪掉了一大把她面前一棵冬青树的叶子。
邺城。
最后一道夕阳将魏砜颀长的影子拉成一竿修竹。
“王爷还在里面吗?”他看了看那紧闭的雕花窗子,哑声问守在门口的军士。
“是啊,一天一夜,水米未进。唉,再大的败仗我们也吃过,可从没见王爷这个样子,魏将军,我们王爷不会有事吧?”
军士隐隐红眼,满面的心痛。
魏砜的眼闪过一丝暗如夜色的哀伤,寂寂然无语,只是拍了拍军士的肩膀,然后要进门。
“魏将军,王爷吩咐过,不许任何人打扰他,否则格杀勿论的!”军士一惊,急忙拦住他。
“没关系,王爷怪罪下来由本将军承担!”
军士点点头,放下心来,末了他道:“那,魏将军,您好好劝劝王爷!”
屋子里所有能够透进光亮的缝隙都被糊实了,人踩进来仿佛置身于一个黑暗的茧子里。
魏砜一时间适应不了这份黑暗,他本能地闭上眼,然后他的鼻子开始工作。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流失,在殇灭,在撕裂,在腐烂,混合甜靡的血腥味,一股令人沉沦的颓废绝望的味道。
“谁?”黑暗的角落里传来一声缥缈虚无的声音,仿佛来自亘古云荒里最让人遗忘的角落。
“是我。”魏砜睁开眼,模糊可以看清角落有个影子,然后他开始小心翼翼地走进。
黑暗中有双痛迷如梦的眼睛望向他,试探着问道:“魏砜?”
“是我!”魏砜柔声答道,单膝跪地轻轻抱住了他的脑袋。
出乎意料的,信阳安静的像个小小的婴儿,任他抱着,在他怀中喃喃而道,对他似乎又对着自己,“我没事……什么事也没有……只是我的心碎了……我一直在寻找着那些碎片,想把它们拼拢起来……可老找不全……”
“王爷……”魏砜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大恸失声。
那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骄傲狂狷男人,他终于被击碎了一切硬壳,将他最最软弱的骨肉组织,血淋淋地展现在了他面前,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如妖一般的男人。
“怎么,你也会流泪?”信阳吃吃地笑了起来,“你可知道眼泪是这世上最虚伪的东西了。就像那个男人,那个男人那些天屈服命运的颓废
、脆弱、无助,原来全是虚伪做作出来的,待你大意的一个转身,他就如虎狼般狠狠噬你一口。这一口真疼,真疼呀,三万三千的兵士,就这么,就这么活活溺毙了,连个尸首也找不到……”
“咳……咳……”说到此间,他双肩抖动,剧烈地咳嗽,然后靠墙如离了水的即将垂死的鱼般,大口大口喘息。
“王爷,你病了!”手下意识地搭在他的额头,烫人的热度,魏砜失色叫道。
“魏砜,来世我不想再遇到他了……因为今生真的够了……”在失去知觉的最后一个意识里,信阳呢喃,有清泪悄然滚落下来,落入尘土,转瞬而逝。
原来最强势的男人他也是人,他也有鲜为人知的脆弱一面!
信阳这一病病势凶猛至极,几经几回的病危,却又一次又一次死里逃了生,冥冥中,仿佛有双无形的手拽住了他总是不安分地想要解脱于身体的灵魂。
七天,烧退人醒,信阳做出了一个全军震惊的决定,退兵。
很多将领极力反对,尤其是魏砜,竟在大帐内与信阳狠狠吵了一架。信阳翻脸无情,将魏砜革职,打了二十军棍,囚禁于暗房内。
第二天,留守边关5万人马,信阳班师回朝。
就在出发前,军士来报,说魏砜昨夜突然失踪不知去向。信阳闻听只是冷冷眯了一下眼,然后抬手做了一个行军的手势。
信阳退兵,望夏得讯,竟也随之退兵,这一战双方都是元气大伤,再僵持下去只会消耗巨大的物资与军饷,于国于民都是不利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