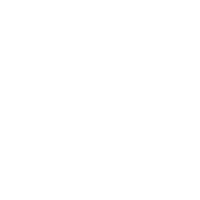“他本是信阳王手下大将,骁勇善战,屡立奇功,但因为得罪信阳王致使未被嘉奖,反而入了死牢!”
“你是说魏砜?”
“不错,正是他!”
义德帝蹙眉,记忆开启。当年大兹与大郢交战,魏砜曾以一队轻骑兵,深入敌穴,杀敌帅将,破敌十万,拥有赫赫威名。只不知如何得罪了信阳,被信阳捏了个罪名,入了死牢,义德帝因为觉着这么个骁将杀了可惜,对于他的定罪一拖再拖,让这魏砜在死牢里呆到今日整整三年多。
“魏砜倒确实是个帅将……”义德帝沉吟。
“若陛下重新启用他,则必感陛下再造之恩,当以身家性命全力以赴!”宰相再次叩奏。
“准奏吧!”义德帝淡淡一句,然后起身下殿。
正午,阳光灿烂。
从监狱门内缓缓走出一个人来,虽然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却依然独显风流之态。
缓缓抬头,眯眼看向那蓝天白云,混浊无神的眼霎那间清明疏朗,三年的拘禁一朝放出,看着这美好的世界,当真恍如隔世。
一抹苍凉的酸涩与讥诮勾起嘴角,双眸慢慢眯起:
王爷,魏砜大难不死,又出来了!
月羲静静地蜷缩在榻上。
青丝铺洒,容颜苍白,像一个蝉蜕了的最脆弱的蛹。
信阳木然立在他榻前,眉心蹙然,眸光复杂地一瞬不瞬看着他。
忽然,他有了动静,一声声破碎而细碎的呻吟从他唇角溢出。
信阳嘴角一牵,流露出一种诡谲的表情,然后从一
个柜子里取出一小瓶子血色的液体,回到榻前,凑近他的嘴徐徐而下,月羲迫不及待地贪婪吞咽,须臾间瓶倾,然后复又沉沉睡去。
用手指拭去他唇角一抹妖冶的红,轻轻放在嘴里,吮吸。
“王爷!”萧筝在身后抱拳躬身称唤。
“打听到了什么?”
“昨日望夏国骤袭,石门关失守!”
“什么?”信阳霍然转身,神色惊痛。
“义德帝任命魏砜为将,带兵十万前去抵御。”萧筝继续道。
“魏砜……”信阳一怔,眸光变得阴暗幽深起来,遥远的记忆开始一点一点渗透入心。
那夜,正是魏砜轻骑军大败大郢十万锐兵之夜。全军上下大开庆功宴,杯斛交错,欢歌艳舞,将士们浑然忘我,痛饮百杯,结果个个醉倒大帐。
信阳亦不例外,卸盔撤甲,散发敞怀,酩酊浓醉,玉山倾倒在书案下。
迷离中似有人抱起了他,将他平放在床,然后吻他。
吻起初带着怯弱,带着颤栗,青涩而笨拙。
舌香滑津甜,喘息细密而酥麻,很快激起迷离在酒梦中信阳的**,他热烈地回应他,使得那人抛却所有顾忌,同他一起疯狂的纠缠。
衣衫尽褪,春色无边,一切都水到渠成,只求寻找一个**的突破口。
紧致的包裹,细细的破碎的呻吟,生涩的回应,逼得信阳全身的细胞舒畅大开,在滔天的欢爱中一次次望见了霓虹。
这是自宠幸男色以来第一次神魂俱授的**,信阳在极致的疲倦里张开了眼看清躺在他身下的那个男人的脸,魏砜!竟是骠骑将军魏砜!
一次欢爱捅破了一切窗户纸,信阳在暗地里大肆宠爱起魏砜。然而信阳并非什么专情的男子,没过多久,又新添了个暖床的美少年。魏砜醋意大发,几次胡搅蛮缠,未能赶走那嬖宠,反而使得信阳对他心生厌恶。试想信阳一向讨厌女子,魏砜如此撒泼胡闹,与庸俗脂粉有何两样?
魏砜伤心绝望之余,竟做了一件惊人之事,在一次战役中竟然违抗军令,使得信阳大受损失。信阳暴怒,当即要杀他。亏得众人求情,才将他罢职,捏了个贪污缴获军资的罪名,押解进京,义德帝当即将他打入死牢。
“魏砜……”信阳低语,重拾起的记忆,往往想的都是那些美好的过往,倒觉着自己从前确实对他有些亏欠了。
“王爷!”萧筝不明白王爷怎么听到这名字表情这么奇怪。
“这真是个好消息”,淡昧的笑挑起信阳的唇角,“萧筝,想办法让我见他!”
“不可,王爷!您忘了,是您将魏砜送入死牢的,他一定恨你入骨,王爷您去见他定然凶多吉少!”萧筝着急道。
“放心,我自有乾坤!”信阳淡笑,眼神里有种奇妙的光芒在闪动。
如霜的月光透过窗棂,辉映在两张无双的清颜上,梦幻迷离地那般不真实。
魏砜修长的四肢巧妙地将信阳锁住,抬起那双妩媚冷艳的眸,饧眼讥诮,“你还真不怕死,竟然敢来找我,你可知道只要我知会一声,你立即便可身首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