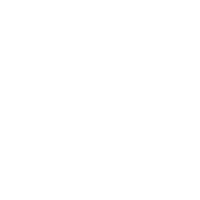“不过我需要有人来写个状子。”浅浅环顾了一眼四周,发现竟找不出一个人来写状子,心中哀叹,此时若是三哥在就好了。
“我来写!”正当浅浅等人为难时,一个衣衫破旧的年轻人从人群中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浅浅面前,躬身行了一礼道,“小生不才,读过几年书,会写个状纸。”
“那真是太好了,云珠,快为先生准备纸笔。”浅浅见着有人愿意出来写状纸,忙欣喜地吩咐云珠。
“不必了。”那个年轻人喊住云珠,撩起自己的衣袍,撕下一角,拿起刀子往自己手掌上划了一刀,竟写起血书来,“这狗官逼死我的母亲和妹妹,又打断了我的腿,既然要告御状,那就要一份有分量的状纸才行。“
”若不能一口气拉他下马,我们怕是不会有好日子过。“这个年轻人一边写着血书,一边头也不抬地说道”我不知姑娘是有什么目的,但是只要能处置这个狗官,还我们一个公平正义,那我今日写的这份血书也算是有些作用。”
浅浅一时无言,看着这个书生洋洋洒洒写满了整张袍角,字字泣血,心中一恸,这是被逼迫到了何种田地,才会写出这样情真意切的血书来。
“看公子文采斐然,想来不是读了几年书这么简单,可是有功名在身?”周明朗看了一眼正在书写的血书,觉得此人应当不简单。
书生正好写完了最后一个字,又在后头签名画押,抬头望着周明朗道,“我本是明德十二年的秀才,在县城谋了个替人写状纸的差事,一日我妹妹为我送饭,正好被狗官瞧见,非要我妹妹做他的妾,我妹妹不同意,竟被他强掳了去,后来送回家的竟是一具冰冷的尸首。我母亲一下子接受不了病倒在床,没多久就去了。我去知府那儿报案,被赶了出来,又去告御状,还未走出宣州,就被人打断了腿,若不是村长差人来寻,我怕是要在山中喂了豺狼虎豹了。”
周明朗气得挥了挥拳头,愤慨道,“此人真是没了一点王法了,连有功名的人也敢动。这还是在京城附近呢,也敢如此嚣张。”
书生敛了敛眉,苦笑了一声,“他背后有人,不然怎会如此嚣张。”
“不就是个贵妃的亲戚,有什么大不了的。”周明朗本来就不喜这个县令,此时更是不屑,“你放心,这次我们一定为你们讨回公道。”
书生点点头,此时已有人自发地在血书上签字,有不识字的,也印了个手印。浅浅见着这一片触目惊心的血红,心里有些不好受,更是坚定了要管此事的决心。
“姑娘,这个狗官还拉了我儿去做苦力,至今生
死不知,三年了,都没见他回来。”一个老太太由一个年轻媳妇搀扶着上前签字画押,然后与浅浅说了一句。
浅浅皱眉,道,“这样被拉去做苦力的人多吗?”